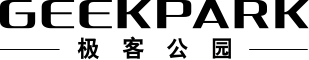「我們的挑戰在于一窩蜂做事,要構建利于創新的文化。」
對話、文 | 衛詩婕、Li Yuan
編輯 | 衛詩婕
當 OpenAI 以 ChatGPT 驚艷世界、成為舉世矚目的創新力量時,中國的創業圈里一度熱議:為什么這樣的創新沒有出現在中國?
創新需要前瞻、定力、和某種程度的賭性。成立于 2015 年的 OpenAI 以非營利機構的姿態出世,在早期,OpenAI 曾鼓勵學者們主動探索各類前沿方向,兩年后,在數億美金即將燒完的刺激下,團隊最終選擇將所有資源和人力聚焦于團隊信仰的技術方向——大語言模型,這才孕育出后來的 ChatGPT。
如果把目光放到中國,一家非營利機構幾乎進行了同樣軌跡的探索,只是時間軸晚了三年。
2018 年,智源研究院在北京成立。獨立于政府、商業、和高校之外,智源從出生便將自身定義為一所民間非營利的新型科研機構——前微軟亞洲研究院創始人之一、剛從金山 CEO 的位置上退休的張宏江主導了這一切。他堅持認為,真正的科研創新需要跳脫出傳統的權力體系、具有真正的理想主義,才可能「加大創新成功的可能性」。
2020年,智源啟動「悟道大模型」系列,是中國最早實踐大模型路線、并堅定下注的機構。那是 GPT-3 剛剛面世的時代,一萬張卡的訓練勸退了中國諸多學者。智源卻堅定地選擇支持一些學者,從 80 張卡追起,調動大量資金以支持訓練大模型。如今,大模型創業潮里的靈魂人物:唐杰、劉知遠、黃民烈、楊植麟等,都曾是「悟道」項目中出現過的身影。
「中國創業者能在這波大模型創業中走向潮頭,多虧了智源這座黃埔軍校。」一位創業者這樣告訴極客公園。
但某種意義上,ChatGPT 的爆火打亂了智源的計劃。
彼時張宏江在美國,再回到國內時已是遍地創業。一夜之間,大模型成為共識。當時,智源一位骨干剛見完幾位要再次出山的創業者,在電話中對他說,「怎么辦,他們一定會挖我們的人。」
「慌什么。」張宏江淡淡地答,挖角在意料之中。
從智源成立的第一天起,張宏江就意識到,前沿探索一旦做成,研究院的人才必定會被挖角——不僅因為商業機構能夠開出更高的薪水,更因為人才的稀缺性。盡管在理智上可以接受,但當這一切真的發生——當一位張宏江極為重視的年輕技術骨干被挖走時——他還是為此「消化了很久」。
自 2019 年起,智源開始花大量時間組建「智源學者」——目的是匯集中國最杰出的人工智能學者群體,并篩選出一波有學術潛力的年輕人,并將資源投入給他們。在張宏江看來,傳統的學術體系對年輕人不夠友好:盤踞于金字塔頂層的學者們虹吸式地聚集了所有資源,而年輕學者在最有熱忱和動力的年齡卻無法真正展開高效的學術研究。
典型的一個例子是,智源青年學者劉知遠在三年前還未評上清華大學副教授,但當他向智源申請立項訓練大模型,當即獲批 10 臺 V100,即 80 張卡以支持他訓練 CPM-1 大模型,這意味著上千萬人民幣的資源投入——「如果沒有智源,以我當時的學術職稱很難調度這么大的資源。」
以反共識的方式支持這一切,張宏江頂住了巨大的壓力——這份決心源自于他的堅信:創新的投入需要堅定,而堅定需要摒棄功利心。
今年 6 月,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們在三里屯璞舍酒店的大堂見到了他。灰色 T 恤衫、短褲、高幫白襪和球鞋,1960 年生人的白發已經爬上額角。這場訪談的不久之前,堅持五年的智源大會終于在今年的 AI 熱潮下成功破圈——Sam Altman、深度學習三巨頭中的兩位圖靈獎學者紛紛空降。
我們不僅聊到了這場智源大會、智源研究院的故事,也談到了這次大模型創業潮中的星星之火,更探討了創新該以何種方式被計劃。
以下為訪談實錄,經極客公園整理編輯后發布:
01
「我們受到的
所有挑戰是自信心的挑戰」
極客公園:成?智源之前,你已經退休了,?且剛從??那樣勞?勞?的地?離開,為什么選擇再次出??
張宏江:從金山退休到做智源,中間隔了差不多一年半,我當時是非常享受狀態的——一邊做企業的顧問,一邊做源碼資本的投資合伙人,同時也能花點時間在美國跟兩個兒子在一塊兒,然后又去周游世界。直到 2018 年夏天 7 月份,一場有關人工智能的座談會在北京市舉辦,會議的目的是探討如何提升當下的科研水平。當時我受邀參與,會上,我提及了美國有個 OpenAI,是一個非營利民間機構,這種形式很新穎。在我看來,國內大學里面研究者雖多,但坦率說,都是一個個小單元,很難集中力量干大事。而企業更多是聚焦自己目前的業務,很難在基礎前沿方向上做足夠堅定的探索。所以當時我提到,中國可能也需要一家新型的科研機構,獨立于高校、企業和政府,追求更系統的大目標。
極客公園:對于打造一個理想的研究機構,你當時有什么想法?張宏江:我當時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能不能做一個社區,把搞人工智能的這些學者都聚到一起,從中找出真正有想法、有干勁的領軍人物。第二步是在社區的基礎上,能像美國的 DARPA 一樣,把他們組織起來做一些事情。第三步才是找到一些目標導向的項目,開始做實。智源也是依照這三步來走的。當然當時我并沒有想自己來做。

智源社區
極客公園:為什么最后決定自己來做了?
張宏江:我找過不少人,問他們愿不愿意做這事;但我后來發現,這其中的難度遠超我想象。接連被拒絕后,就這么半推半就,我自己做了理事長。
極客公園:難度在哪里?
張宏江:要做前沿的科研會涉及大量的資金,前沿的科研探索也不是一定能成功,敢不敢賭這東西,能不能堅持、堅定地判斷,對研究的管理人員是真正的考驗。2020 年 6 月,GPT-3 發布后,智源當時決定要把所有資源和人力聚焦在做大模型——也就是后來的「悟道」大模型系列。大模型當時在學術圈還是比較另類的一條路線,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悟道發布后,有人一看智源花這么多錢,就有一些噪音說這個方向不對,甚至說智源的決策不清晰、產出不清晰、將來的(發展)不清晰。整個智源包括我,都頂著很大壓力。
極客公園:那時候的確有傳言說智源是騙錢的。
張宏江:智源受到的所有挑戰都是對于我們自信心的一種挑戰。悟道 1.0 已經花了不少的資金,2.0 要想真正讓所有人能用,還需要工程的力量——我們當時的預算根本不夠撐這件事。要往下走,就需要更多的錢。

但如果回看我們 2022 年 6 月份做的計劃,70% 的預算就用來做兩件事:大模型和支持大模型的架構。按照我們的路徑圖:希望 2023 年的 9 月份大語言模型能夠上線,在這基礎上,能做一個對話機器人——這與 OpenAI 的路徑是一致的,GPT-3.5 就是大模型,ChatGPT 就是對話機器人。所以今天回看,我們的路徑圖可能是對的,只是說我們比它晚一年。不過 ChatGPT 的發布,的確帶動了整個業界的行動節奏,也一定程度上打亂了我們的節奏。
極客公園:我挺好奇,ChatGPT 爆火后,你真實的心境是怎樣?
張宏江:ChatGPT 發布時我在美國。我意識到這個事在中國可能會非常熱鬧。回來之前我在想,或許我們可以像 OpenAI 一樣,組個團隊把這件事做成公司。但我回國后兩三個禮拜,中國已經遍地是(大模型創業)公司了。當別人做成功的概率可能比你還高時,你為什么還要湊這個熱鬧。
極客公園:這是一個冷靜的過程?
張宏江:對。我很快靜下來了,覺得 ok 至少我自己不用搭團隊去做了,他們要搭團隊他們就去做,我能幫就幫。
極客公園:但在幫(別人創業)的過程中,智源被挖角了。
張宏江:一個年輕人的離開讓我憂郁了很長時間。他是我們很強的一位技術骨干。而他被挖走恰恰就是因為我曾經當著那個創業者的面狠狠夸獎了這個年輕人。
極客公園:你有挽留他嗎?
張宏江:當然挽留他了,一方面我挽留他,另一方面我也鼓勵他,因為他有他的夢想,又年輕,可以試錯。
極客公園:聽說你消化了挺長一段時間。
張宏江:對。我希望那個年輕人能在這兒接著再做兩年,他可能就能做出世界領先的多模態大模型了。我問他,你想做一個公司的工程 VP 或者是 CTO,還是想做一個科學家?
極客公園:他怎么回你?
張宏江:他選擇要做一個 CTO。(邀請他的)那是一個很被人看得上的創業者,所以從這個意義上我會很理解他。
02
「當他們三個人
判斷一致時,我就信了」
極客公園:你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到 OpenAI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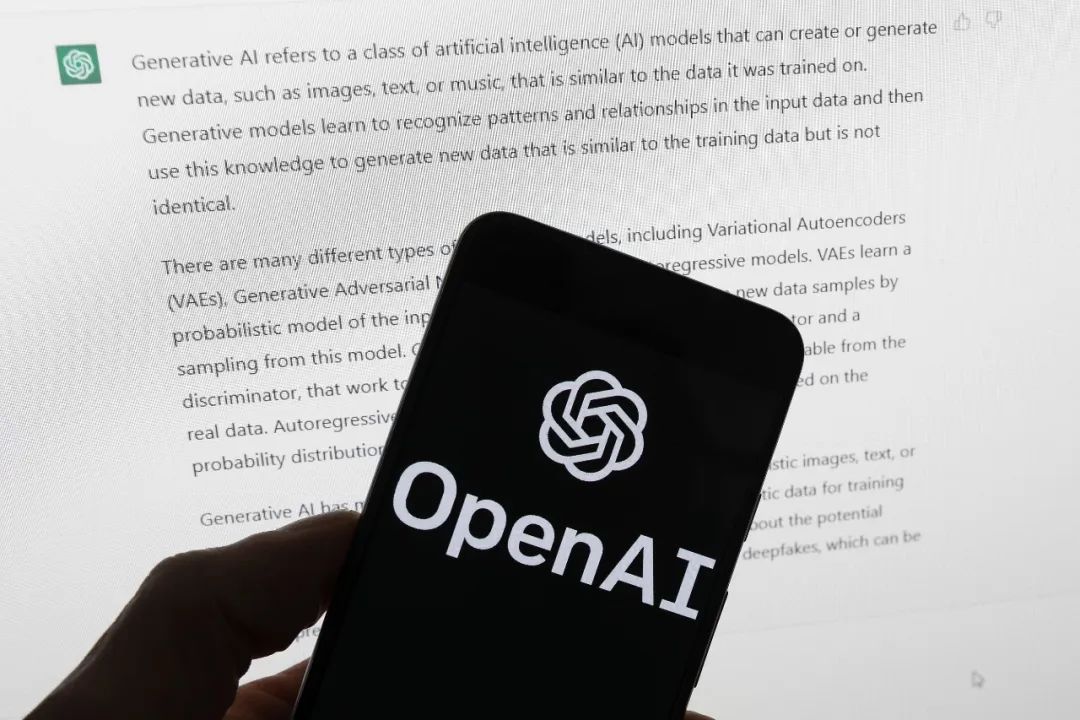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張宏江:2016 年底我決定退休后,去硅谷游學的時候,曾經在伯克利和 OpenAI 做強化學習的團隊聊過。他們創始的使命就很清晰,AI 作為如此重要的一個改變人類的技術,不能讓一兩個巨頭所壟斷(主要指谷歌)。坦率說,當時我不覺得他們能成功。但是我喜歡那種非營利組織的組織方式——不附屬于一個企業,又不附屬于一間高校,也不附屬于一個政府。游離于所有的功利圈之外,又專注于做一個方向。
極客公園:當時想過「這事能在中國干」嗎?
張宏江:我當時就想過,但我覺得可能得十年以后,等到某個富豪能夠想通了,把錢拿出來(做這件事)。結果在 2018 年,機緣巧合下,智源就成了。
極客公園:OpenAI 早期經歷了從研究方向的發散到收攏,最終選擇大模型方向 all in 資金和人力;智源也經歷了一個類似的過程?
張宏江:我們在 2019 年底就開始討論,希望從我們當時所有研究方向中(機器學習、信息系統、數理基礎、系統架構、芯片),能選出一個聚焦的方向。這事到 2020 年 GPT-3 發布時變清晰了:鐵軍、唐杰、劉知遠、文繼榮這些在我們平臺上的學者,大家意識到這是一個(里程碑),所以我們很快就搭出一個團隊,機器學習和信息系統兩波人一起來做這件事,開始做「悟道」大模型系列。現在大家會認為 GPT-3 是一個里程碑,但事實上,當時所有科研部門、四小龍等公司,可能感知沒有那么強烈。
極客公園:那你們為什么堅信(大模型)這個方向?
張宏江:我是在悟道 2.0 發布時信了這件事——因為 GPT3.0 它再強,它是別人做的,我們自己復現出來,路子就走通了。在此之前我并不是徹底不信。因為我自己并沒有把這個算法本身從頭到尾走一遍。作為一個科研的管理者,你自己并不一定是這個領域里面最強的專家,但你要能找到這個領域最強的專家,并百分之百地信任他們。當他們幾個人,智源的兩位院長,黃鐵軍和唐杰,加上文繼榮和劉知遠等智源學者,都跟我說這件事(值得堅持)的時候,我就信了。
極客公園:我之前有機會跟文繼榮老師聊過,他說在 GPT-3 出來時,國內真正懂 AI 的這些人已經開始意識到大模型這條路是能走得通的,接下來只是工程問題。
張宏江:我認為大家那時候還是懵懵的,因為 3.0 并沒有很強的涌現能力,大家只是認為這個方向值得探索。至于大家能不能看到 GPT-4,或者能不能看到跟 AGI 的這種(聯系),我想那是很遙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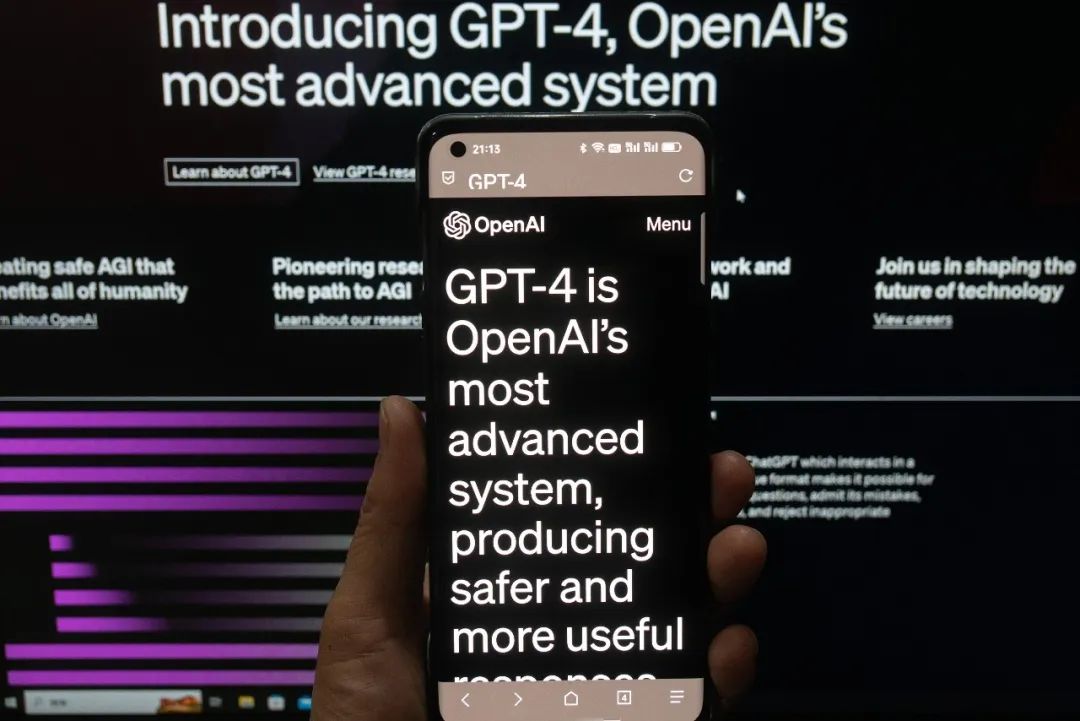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極客公園:他有提到一點,那個時候包括智源在內,國內有幾個團隊已經開始立項要做大語言模型了,但這些團隊沒有足夠的信仰把這事堅持著非常認真地做下去。
張宏江:這個我同意,但我只同意一半。把時間撥回到 ChatGPT3.0 發布時,我們確認這件事值得做,但也意識到需要大量的資源,而獲得這樣量級的資源并不容易,智源當時拿出一半的經費來購買算力。算力和招人都需要錢,只能在兩者之間取舍。招人也有困難,你跟別人說「我們做大模型」,大家未必有共識,很多人會問「三年以后智源還在不在?」。我們回頭看一個正確的決定,會覺得理所當然,是一個無比清晰的決策;但過程中的每一步決定與堅持,其實都伴隨著大量混沌的綜合因素——尤其科研領域重大投入的決策是無法篤定預測結果的,充滿驚險與冷暖自知。
極客公園:你自己內心覺得三年以后,這個機構還會在嗎?
張宏江:我想我會以我的努力去爭取這件事。堅持做正確的事情,就會有生命力,有生命力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有一切。
極客公園:你覺得是什么造成了今年年初中國在這波?模型潮中的失聲?是信仰,還是資源不足?
張宏江:對智源來說,的確是因為當時的資源不足。其他大公司沒有做出來,也許是勇氣和認知的問題,又或許是其他原因。
03
「成為黃埔軍校
對我來說是成功的標志」
極客公園:大模型創業圈現在總談智源系,智源就像一個原點一樣,向很多創業公司、大廠發散出影響力和人才,輸出了技術譜系。但這些人才都是你辛苦聚集起來的,理性上和感性上分別是怎樣接受這件事?
張宏江:二月份,智源一位副院長打電話給我,說幾位連續創業者要出山做這件事,肯定要挖我們的人。我說我們在做智源的第一天就應該想到了,(智源)做成以后我們的人一定會被挖角。我第二句話說的是,微軟研究院過去20多年都是被挖的,但并沒有把它挖垮。總有一些想做研究的人,他們不會受到商業的干擾,我們總還能吸引一些有理想主義情懷的人。 另外,至少我們可以說,北京的這個圈子里真正做過大模型的都是在悟道(這個項目)里做的。這是我們可以得意的地方。
極客公園:聽起來智源像一個黃埔軍校,你愿意它變成黃埔軍校嗎?
張宏江:成為黃埔軍校對我來說是一個成功的標志。如果智源的一些人到了某些公司成為了核心骨干,把公司做成了,我會非常開心。我們的代碼、我們的系統被別人用來做他們的產品,做得很好我也會非常開心,這本來就應該是一家非營利研究機構的價值所在。另外我也希望我們的一些成果能成為基石:比如我們不斷有開源的模型出來,大模型開源技術體系出來,這些模型能成為公司或其它研究機構下一步研究和開發的基礎。
極客公園:您提到微軟亞洲研究院,之前我跟小冰的李笛也聊過,他們那批人最終選擇出來是想干一番事業,原來在研究院仿佛已經能看到退休以后的狀態了。
張宏江:這其實是兩件事。在我看來,如果你的志向是做研究,那么當然可以在研究路徑上做出自己的突破,研究本身就是一項可以投入一生的事業;你不斷地有新的算法研究出來、有新的系統研發出來,你本來享受的就是這個過程,可能只是沒有做公司賺的錢多而已。
極客公園:找到那些真正有志成為一流科學家的人更難,還是說服他來到智源更難?
張宏江:第二個更難。發現一流的科研人員并不難,你看看最好的學者會議上發表好文章的是誰,誰在參加會議,一目了然。但能不能說服他們來,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拒絕智源的人太多了。我跟他們每個人都說得很清楚,我希望他們加入,我會盡我所能支持你在智源踏踏實實做三年。
極客公園:為什么這個數字是三年?
張宏江:因為三年能真正讓你在研究上開啟一件事。
極客公園:可是僅僅做成一件事,僅僅用三年的時間成為不了一流的科學家?
張宏江:不,這件事如果他做得很漂亮,可能是一個系統,可能是一篇文章,讓別人看出他的能力。他帶著別人對他的這種信任,到任何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做成事。另外我也有一些自信,如果他們三年做得很成功,也許就不愿意出走,就會繼續做五年十年。
04
「好的資源要
留給青年科學家」
極客公園:悟道早期花了非常多的資金,應該有上千萬(人民幣)。一個中國的青年學者能有多大機會運作這么大的資源?
張宏江:大模型的研發確實需要大量的資源,學校里的學者們,尤其是青年學者,是非常難拿到這樣規模的資源的。
極客公園:你在智源一直強調,好資源要留給青年科學家。這種想法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有的?張宏江:一開始就有。我在這方面一直有偏見:中國 30 歲左右的學者的基礎、學習能力、見識,都是老一輩難比的。今天我也是屬于老一輩的,所以我也更希望跟年輕的人一起做事。在中國的科研體制內,盤踞在金字塔頂端的老一輩學者虹吸式地聚集了大量資源。所以,智源從最開始就組建智源青年學者系列,目的就是要把資源給年輕人,讓年輕人挑大梁。這中間智源,尤其是幾位院長花時間比較多的,是把優秀的年輕人找出來,給他們充分的資源,支持他們堅持做最有想象力、最正確的事情。
極客公園:今天在談話當中您很多次提到了對年輕人的相信。這種相信最早源自于什么時候?
張宏江:畢業后,我待過三個國家,丹麥,新加坡,美國。尤其在美國的文化里,大家很希望給年輕人空間和機會,去試錯或者去冒險。我本人也是這種文化的受益者。另一個更強烈的因素是,中國過去 15 年互聯網公司里成功的年輕人太多了,在他們身上你真的看到了這波年輕人的潛力和實力。在創業上是這樣,在研究上也是這樣。有美國那種文化對我的影響,也有中國過去 30 年的發展變化帶來年輕人的陽光,見識,冒險的精神和能力,增強了我的信心。我持續地從年輕人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也更多地了解這個社會十年二十年的變化,有時候我們在我們同齡人的圈子里是看不到的。
極客公園:您經常說舞臺要留給年輕人,德高望重的老科學家都已經不在一線了。但您也是 1960 年生人,是一個德高望重的人,這會不會有點矛盾?
張宏江:我覺得不矛盾。我從第一天開始就告訴智源所有的人,智源所有的文章都不署我的名字。

圖片來源:智源研究院官網
這里深層的意義在于,我希望我們這些已經過了事業高峰的人不要再去跟年輕人搶資源和名譽了,我對每位院長也有類似的要求,絕不止自己沒有實質貢獻的文章上署名。
極客公園:所以你是要當那個給年輕人搭舞臺的「老人」?
張宏江:可以這么說。
05
「如果把智源變成營利,
我們跟滿大街的
創業公司就沒有區別」
極客公園:OpenAI 也進行了架構調整,其主體公司仍然是一個非營利機構,將子公司部分商業化,實際上 ChatGPT 正是出自于這家子公司。這樣的結構對你有沒有啟示?
張宏江:回頭看看這種架構設計的本身,你會再次敬佩 Sam 這樣的理想主義者。第一 Sam 個人不占股。第二,這種設計本身是為了做成一件事而不純粹是為了賺錢。正因為他知道做成 AGI 這件事需要很多錢、很多人、持續做很長一段時間,雖然他自己是理想主義者,但他并不要求所有人都是理想主義者,他給參與者設計很好的回報——子公司的使命就是盈利,讓投資人賺 700 倍還是多少倍就走人,公司就回到非營利。

OpenAI 創始人 Sam Altman | 來源:視覺中國
很多人跟我說,我們智源能不能這樣做?我說我當然希望這樣做,但是今天只要我們開始融資,開始把自己非營利變成營利,我們就會時時面臨投資者的壓力,就跟今天滿大街的創業公司沒有區別。不要忽視一點,OpenAI 做這件事比別人早了三年,它已經屹立潮頭,已經形成壁壘。而我們并沒有。
極客公園:是因為競爭力不夠,所以智源目前才不考慮走商業化的道路?
張宏江:盡管我們在中國比別人早認識到這件事,積累了算法、多了一些數據,但簡單追隨 OpenAI 路徑,顯然是沒經過獨立思考的懶惰。跟風這件事,你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為什么跟風,能不能跟。如果我們三年前想這件事,也許我們自己能走通。今天你再走別人的這條路,就可能走不通。不冷靜的商業化反而讓我們產生焦慮感,會讓我們偏離方向。因為你只要有融資就必須得有商業回報,你能不能給投資者帶來回報(是未知數)。
極客公園:我聽說最近在智源內部,也有人在討論智源要不要走商業化的路線。你覺得大家為什么會這樣提?你擔不擔心外部的商業環境,會影響智源好不容易構建起的氛圍?
張宏江:的確有很多人問我,有人甚至說,智源趕緊要做一個公司,要不然人會流失,要不然拿不到資源。我同樣反問:那我們跟大街上其他的創業公司有什么差異化?
極客公園:如果他反問你,我們為什么要區別于別人?
張宏江:我就說你可以參加別人的公司或是創立自己的公司。我們還是非營利的一個研究機構。我會跟很多年輕人很耐心地解釋,我們只能不斷地耐心地去尋找同路人。
極客公園:經過這波熱潮之后智源接下來會怎么發展?
張宏江:和一年前我們想的一樣。找一波有理想主義情懷的人,他愿意拿出三五年做一件事,不為了股票和物質回報,僅僅是享受做事的過程的這樣一撥人。我們還希望在系統上能做一些突破,希望你會看到我們的多模態模型進步也會很快。
極客公園:OpenAI 依然還是智源的榜樣嗎?
張宏江:是,還會是智源的榜樣。
06
我趕上了每一個
中國轉折的最佳時間點
極客公園:智源大會堅持做了五年,今年有了破圈的跡象。能感受到大會的學術品位,那天在現場我們也留意到一些細節,比如全程用英語交流、現場也沒有那種 VIP 式的沙發座。

2023 北京智源大會嘉賓海報
張宏江:對。大概在這次智源大會的三四個禮拜前,我又看到了某個學術會議的報道圖片,前面放了一排沙發,我把照片發給同事,我說確保我們第一排的凳子和后面的凳子沒什么區別,只是貼一張紙條劃分一下 VIP 嘉賓的區域。這些細節我會很留意,因為我希望這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會議。
極客公園:你提到過你很喜歡《異類》那本書里的一些觀點,簡單來說就是時代造就人,一些時代關鍵的轉折點會密集地出現一波改變社會、改變世界的人。你身上的時代烙印是什么?
張宏江:非常幸運,我的每一個轉折都趕上了中國轉折的最佳時間點——正好高中快畢業的時候高考恢復了,很幸運,考上大學了。等我本科畢業時,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了,可以出國了。在國外待了十幾年以后,中國本身經濟發展,讓我想回來了,于是找到了微軟亞洲研究院的機會。每個點都踩對了,這和《異類》那本書是完全一致的。
極客公園:你年輕時想做一個一流科學家,還是一個 CTO ?
張宏江:我想做個一流科學家,雖然我沒做成。
極客公園: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的科研投入基本跟美國持平了,至少我們看到官方的數字這樣顯示。但目前大家感覺效果不如美國?
張宏江:斯坦福每年會有一個報告出來,AI index,會統計 AI 文章的發表總數。從數量來看,中國是碾壓美國的。發表 AI 文章最多的十個機構,麻省理工你猜排在第幾?排在全球第十,前九名全是中國的——顯然,我們的 KPI 鼓勵了數量,而質量和數量的不匹配是因為我們真正的創造力不夠。而且把那些文章分分類,你就會發現哪一個領域熱,這個領域的發表數就多。這樣你的前瞻性就不一定夠。
極客公園:有沒有想過怎樣改變這樣的氛圍?
張宏江:做智源這件事,我們希望通過幾年做下來,我們的成果會更好,能吸引更好的人,這波人就是可以改變未來的。這樣的堅持本身就是在改變整個科研環境和水平。
極客公園:智源的追求還是要在研究上做出突破性的東西?張宏江:對。這是我們一開始的使命。其中的難點也在于,你在一個功利、非常浮躁的社會里怎么把這件事做下來,這也是讓人興奮的地方。
極客公園:您在學界、商界、投資界都待過,這些圈子相對來說很系統、有各自的規則。但今天的談話你不停地重復理想主義,也一直在強調一種純粹感?
張宏江:如果你知道我在評價投資項目時的冷靜,你會覺得我是如此(像)商人。理想主義與現實并不矛盾。我們的社會需要一些人認準一些方向,動用一切資源去做這個事。這些事情本身沒有太多的理想主義色彩,而對現實世界又有著非常實際的影響。科研要想有效、能夠真正地突破、能夠持續地引領(趨勢),這些本身就需要務實的做事方式。我在罵人的時候是看不出理想主義形象的,完全是非常非常實用的。
極客公園:你不會給自己貼上一個理想主義的標簽?
張宏江:不會。
極客公園:為什么?
張宏江:本質上我希望用正確的方法做正確的事。只是在今天的形勢下,用正確的方法來做智源(研究院),這看上去比較理想主義,僅此而已。
彩蛋
這次采訪之后,張宏江開啟了為期一周的英國之旅,結束之后他發了一條這樣的朋友圈。

從 0 到 1 的過程,是令宏江沉迷的選擇路徑,重要的是不斷起身看向下一個問題。
追問
極客公園:你怎么看現在的這一波大模型創業潮?
張宏江:我覺得一定有人做成,一定有平臺公司能夠做成。
極客公園:有比較看好的創業者嗎?
張宏江:我不適合評價。
極客公園:接下來中國的大模型,你覺得可能挑戰會有哪些?
張宏江:挑戰很多,有一些大家都想到的,比如算力,人才,數據。但我會覺得一個更大的挑戰在于,一窩蜂做事(就像之前很多時候那樣),這是我們跟美國在創新效率上競爭的一個劣勢。
在美國,當一個領域里,大家看到有很強的領軍者在往前走時,大家不會去重復他做的事,而是會尋找差異化。這使得整個創業生態還比較健康、有效。我們的一窩蜂會使得資源被分散。我希望我們的文化可以幫助創業者成長得更加理智和健康。
*頭圖來源:智源本文為極客公園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系極客君微信 geekparkGO